人工智能時代:文藝評論何為?

我從事的是視聽評論工作,這項工作的特點是兩個“大”:第一個“大”是評論對象數量龐大,從電視劇、網劇、綜藝、動畫片、紀錄片到微短劇等,可謂五花八門、包羅萬象,難免顧此失彼;第二個“大”是觀看量巨大,比如說一部電視劇動輒三四十集,常常追劇追到兩眼昏花,而只有觀看量足夠大,下筆才能更有底氣。隨著人工智能興起,我深刻地感受到這種科技所帶來的極大便利,它能在短時間內根據我的要求擬出評論提綱,查找相關的資料,也給我一些思路上的啟發,可以說,既解放了我的雙手,也拓展了我的視野。
以我撰寫評論的一部熱播的帶有科幻色彩的現代偶像劇為例,我讓人工智能分析它在創作上的創新之處。它大概在15秒之內就從題材選擇、敘事結構、人物塑造、主題表達乃至營銷傳播等方面都做了分析,雖然文字篇幅不長,但是基本上言之有物,且帶著專業術語,作為一份提綱,它完全是合格的。我再查找網絡上相關的文藝評論,發現已經有不少自媒體刊發了這部劇的評論。這些評論雖然不少帶著營銷性質,話語模式比較套路化,但是已經逐漸將大多數真人撰寫的文藝評論淹沒其中。
今后還會有人看專業評論嗎?除了主流權威的文藝評論平臺,一般人撰寫的文藝評論還有傳播機會嗎?人工智能既然如此迅捷、全面,真人文藝評論還有哪些優勢?想到這里,我們這些專業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會感到有些恐慌,正如很多分析預測的那樣,未來很多工作崗位將會被人工智能替代,那么文藝評論是否會被替代?我想,就像文藝不會被人工智能替代一樣,文藝評論也不會被替代。相反,在人工智能時代,將更加凸顯專業文藝評論的重要性。原因何在?因為人始終是藝術創作主體,而人工智能評論始終缺乏藝術創作的主體性、主動性,更缺乏價值判斷能力。
缺乏主體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缺乏個性和深度,導致評論內容趨于同質化。追溯人類藝術的起源,有巫術說、勞動說、模仿說等觀點,但歸根到底是情感與理性的交織,是人的主體性精神的充分彰顯。文藝評論亦然。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講:“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是說,評論者要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審美體驗,對作品進行創造性的闡釋,而不是簡單地復述作品內容。而人工智能評論只能基于數據和算法生成文本,無法真正“感受”作品中的情感或藝術價值,這必然導致缺乏將抽象轉化為具體意象的能力,文章深度和個性不足,文字也顯得冷冰冰的。究其原因,文藝評論往往需要評論者從主觀感受出發,結合個人情感、經歷和文化背景來解讀作品,正所謂“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特別是有些文藝作品往往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中,而人工智能基于訓練數據中的已有內容,本質上是已有評論的重新組合或模仿,并非真正的原創思考,更別說人工智能難以捕捉作品中的隱喻、象征和隱含意義。
比如,我請人工智能嘗試撰寫一篇關于一部熱播的講述安徽地區家庭故事的年代劇的評論,它能分析出作品中出現的建筑、街道、大院、美食等蘊含的安徽地域文化符號,也能分析出姊妹之間相互幫助的情節,但是,它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所經歷的獨特的歷史情境,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的人為何對生男孩有那樣的執念,以及為何會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中塑造出獨特的家庭情感與鄰里情感。而理解這些,需要對當時的歷史和當地的風俗有著深刻的認知,這顯然是人工智能無法勝任的。
缺乏主動性易于理解,就是人工智能評論都是被詢問出來的。愛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準則更加適用。人工智能文藝評論的質量往往取決于提問者的問題,提問越精準、深刻,人工智能生成的文藝評論也就越專業。這反過來也證明,提問者實際上需要具備深厚的評論素養和美學素養。從當前人工智能文藝評論發展趨勢來看,它們的問題不在于答案太少,相反,是答案過多,且所有答案都是預設的,缺少獨特視角。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文藝創作是作者精神活動的產物,而文藝評論是評論者對作品進行理解和闡釋的過程,同樣需要發揮評論者的主觀能動性。好的文藝評論往往源于對文藝現象和文藝作品的主動關切,主動介入創作,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良好互動,而非等待人為喚醒。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現實的仿像,是人類在洞穴墻壁上看到的反射影像,與現實本就隔了一層,而文藝評論又是在對這種投射的再闡釋,與創作又隔了一層。應該說,人工智能能深入參與藝術創作,但是對于文藝評論而言,就更像隔岸觀火,缺乏自主的熱情與碰撞。
最后,缺乏價值評判。中國文藝創作歷來重視文以載道,文藝評論同樣如此。“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好的文藝評論始終是推動文藝創作的利器,是引導文藝創作的重要方向盤。特別是近年來,我們更加重視文藝評論的制度化設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隨著時代發展,文藝創作乃至文藝生態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進一步發揮文藝評論的“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的價值引導作用。這里的價值,既包括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藝術價值,也涵蓋其社會價值,也就是作品所蘊含的“成風化人”的價值。而人工智能評論最缺乏的就是價值引導能力。它們往往能分析出作品創作上存在的缺陷,比如敘事節奏拖沓、人物動機不足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是一旦涉及一些較為隱含的價值觀偏差問題,人工智能往往無法察覺。例如,有些作品收視率、點擊量很高,但在價值導向上卻并不見得正確,有的只是為了滿足受眾的“爽感”,卻與主流價值觀相悖,甚至帶有錯誤引導,人工智能往往難以甄別。這就需要評論者對主流價值觀的熟悉掌握,這既包括對政策文本、意識形態、主流價值的深刻把握,也包含對未來趨勢的研判,同時還要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等,這些都是人工智能無法比擬的。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部家庭年代劇,最后我撰寫的文藝評論并沒有采用人工智能給出的思路,而是從自己的感性審美出發,結合自身對家庭親情的體悟創作而成。正如藝術創作需要擁抱人工智能,文藝評論同樣要積極擁抱人工智能,但是必須明確的是,在人工智能時代,人依然是萬物的尺度,始終是衡量文藝創作內涵與審美最重要的標準,對此必須保持充分的自信。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藝創作,我們既要憑借傳統文藝評論權威性、專業性引領方向,同時也要發揮人工智能的優勢,提升文藝評論的時代性、科學性,從而更好地推動藝術創作。

理論新聞精選:
- 2025年04月04日 11:56:17
- 2025年04月04日 11:44:28
- 2025年04月03日 09:42:15
- 2025年04月02日 16:46:51
- 2025年04月02日 10:2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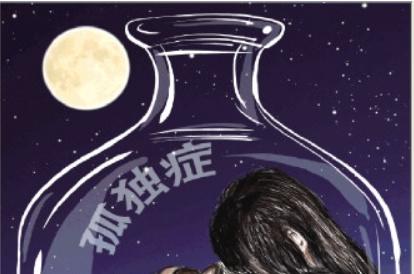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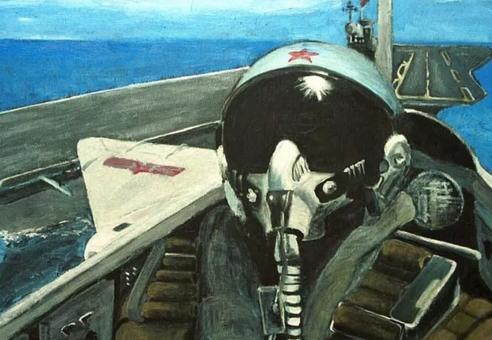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