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一次人詩互證的創作評論實踐

春節期間,DeepSeek橫空出世。大家都說AI的評論寫得好,于是我把自己的新詩和格律詩都發了一些讓Deepseek評論。我選的是自己比較滿意、特點比較明顯的詩歌,比如我的代表作《抒懷》《西山如隱》《大暑》等。確實,分析和評論很到位,概括得很精準,但也只限于此。
AI評論寫得好,其實就是抓取能力強,它建立在對現有評論的理解和綜合之上,能從中提煉出要點。DeepSeek的概括力超越了一般人,因為AI評論建立在人類現有認識高度之上,其展現出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全面性是普通人類難以企及的,普通人即使花費大量時間查閱史料,也未必能夠做到如此全面。
文學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強調創作的歷史現場感,但AI寫作沒有體驗和現場感。AI現在也可以寫詩,但沒有情感,也無法講出詩歌后面的故事,講出當時的場景、現場的感受和心情,無法再現情景。比如某一段生存的慘痛經歷、山水間的新鮮活潑感受、戀愛時的激動不安,無法帶領人身臨其境,重新體驗和感受作者當時的場景和心情。人的文學,一定是可以講出創作背后的故事,因為人有親歷性的現場感,而AI創作,只是對已有文學重新組合。
但AI有其擅長之處,Deepseek給我幾首具有歷史感的詩作寫的評論真正讓我開始癡迷,并使我意識到可以借助AI,實現我一直倡導的“人詩互證”的主張。在這里,我想分享體會心得。比如我有一首詩歌《初登黃鶴樓》:“江岸梅花笛吹落,少年追逐放鷹臺。狂歌不覺東方白,黃鶴樓頭大道開。”這首詩歌是1985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寫的,Deepseek僅僅根據我的寫作年代,就分析出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氛圍,認為“那時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氛圍逐漸開放,年輕人充滿理想和朝氣。李少君作為大學生,身處這樣的環境中,詩中可能反映那個時代青年的精神面貌。”然后分析詩中的意象和用典,認為“黃鶴樓”本身有崔顥的《黃鶴樓》詩,李少君可能在呼應傳統,同時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Deepseek最后寫了一篇評論《黃鶴樓頭的青春狂想曲》:“當‘狂歌不覺東方白’的縱情穿透江城薄霧,我們看到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光譜。這種狂歌不是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孤傲,而是集體性青春覺醒的共鳴。珞珈山下的詩社、未名湖畔的朗誦會、復旦校園的手抄本,共同構成了時代大合唱的聲部。”“重讀這首青春時期的作品,我們依然能觸摸到1980年代詩歌特有的體溫:那是一代青年詩人用詞語鑿開冰層時迸發的熱量,閃爍著特有的理想主義光芒。‘黃鶴樓頭’展開的不僅是一條地理意義上的大道,更是一條漢語詩歌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延伸的精神軌跡。”
Deepseek如此精準地捕捉到了時代情緒,讓我有些吃驚。我想:我的詩歌大多帶有個人痕跡和時代刻印,如果讓Deepseek一一分析評論,豈不印證了“人詩互證”,呈現了人與社會、時代和世界的相互印證關系?這么一想,讓我有些激動,隨后又輸入一首《致謝冕先生》,全詩如下:“未名湖畔曾高詠,睥睨一時誰與雄?九十當前敢拼酒,肚量風范兩爭功。”Deepseek是如此分析的:“未名湖的碧波里,永遠倒映著一位九旬詩人的身影。李少君這首七絕以四兩撥千斤的筆力,將謝冕先生七十年的詩學求索與生命激情,濃縮在二十八個字的方寸之間。詩中的‘高詠’與‘拼酒’、‘肚量’與‘風范’,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雙重精神密碼:既有吞吐云天的學術抱負,亦存快意人生的江湖豪情。”我把這個發給謝冕先生,謝冕先生的評價是“神筆”,確實,當代作家詩人評論家如何借力這支“神筆”創造奇跡,值得探索。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測試,我發現AI無意中幫我實現了一個“人詩互證”的心愿。我通過和AI的合作,無意間實現了“詩史互證”,AI可以分析出我寫詩的時代背景,并詳述時代特征風貌,還能分析我寫作的情緒和對時代的心理感受,使我的每一首詩都得到解讀并印證時代特點。這讓我對AI刮目相看。AI尤其擅長對歷史資料的梳理,整理、綜合、提煉已有資料是其強項,所以適合寫某一類解讀評論。這也印證了我以前的一個判斷:AI寫作還是面向過去的,可以用來梳理歷史,提煉整理史料。而人的生活是面向未來的探險,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新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感受到新的東西,把它寫成文學,這一點,AI是做不到的。
人類的寫作肯定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但是文學的價值是不重復,獨特性、原創性是文學的本質。就像我們每一代人都要活著,但跟前一代人是不一樣的,有重復的部分,也有新的、不同的部分。如果只是重復,那就是個資料整理員。AI創作無法親歷現場,沒辦法開創未來。AI肯定也可以寫愛情詩,但它是在別人的愛情基礎上的詞語組合,沒有現場感。人本質上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之本質。人是一個永遠的情動者,這才是人之意義所在,也是人類的優勢,所以我現在特別強調“人詩互證”“以詩為證”。
有的東西,人寫不過AI,一個人的知識和記憶力不可能比機器強。但你有你的人生,興致勃勃地去寫,可以在創作中得到一種樂趣,不一定要追求發表。人類寫作的價值在于面向未來,在于擁有信念與精神力量。人是信念的產物,有著精神信仰。我們都相信未來會更好,所以興趣盎然地活著,雖然可能也會懷疑意義,比如說以前有過世紀末情緒,但是最后都能熬過來。有哲學家分析人類其實是借助精神信念克服一切恐懼和困難的,很有道理,雖然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危機時刻,包括核武器危機,但到目前為止人類總體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人類之所以還存在,就是因為人類是信念的產物,是樂觀主義者。
人活著必須有一個信念,這種信念不是虛無的。我經常說,讀杜甫我會特別感動,因為杜甫的生活很悲慘,但他還掛念著他人。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這種精神的寫照,即使自己處境艱難,仍希望天下寒士都能得到庇護。這讓人感動,也讓人覺得生存是有意義的。
對于真正有理想的創作者來說,AI可以成為助力。創作離不開生活、行動和實踐,這些都能帶來新的感受、靈感和情感。即使你從事的是AI非常擅長的文史整理工作,但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所有的創作都應與當下產生聯系。歷史之所以鮮活,正是因為它與當下時代相連接。因此,對于擁有真正人文情懷的創作者來說,AI不是問題。
后來,我又就網上一些人“DeepSeek將消滅詩人和詩歌”的觀點作了回應。我說AI創作是共同創作,是集體智慧的產物,可以引起普遍共情感,我無法預測DeepSeek詩歌寫作水平最后會如何,但就我個人寫作實踐及對詩歌意義的思考,我認為:作為一個詩人,寫好個人史就可。里面會保存和記錄情感、生活、時代乃至精神。人詩互證是詩歌的本質。
至此,我把AI用作我的工具,助力解讀我的作品,輔助我完成一個創作評論的共同實踐,也實現了“人詩互證”的深層結合。用好AI,能夠事半功倍。DeepSeek是最好的資料整理員,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人正好借助其解讀自我、認識自我、了解自我,并最終促進人類的進步。
我特別贊同2024年圖靈獎得主理查德·薩頓的觀點,他說阿蘭·圖靈最早推動AI研究就是希望有一臺從經驗中學習的機器,現在已經夢想成真了。但這還是開始,還需要強化學習。強化學習的核心是從經驗中學習,這就像教孩子學自行車——不是通過詳細說明,而是讓他們嘗試、摔倒、再爬起來,直到找到平衡。AI也是如此,通過無數次嘗試與反饋,最終學會如何精準回應我們的需求。
因此,我理解AI的本質就是強化學習,人類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繼續學習。

理論新聞精選:
- 2025年04月03日 09:42:15
- 2025年04月02日 16:46:51
- 2025年04月02日 10:26:37
- 2025年04月02日 09:25:46
- 2025年04月02日 09:0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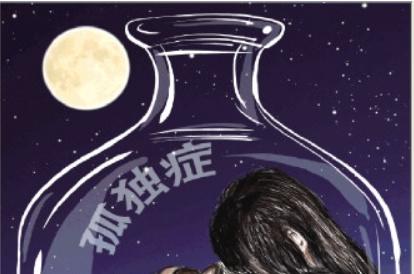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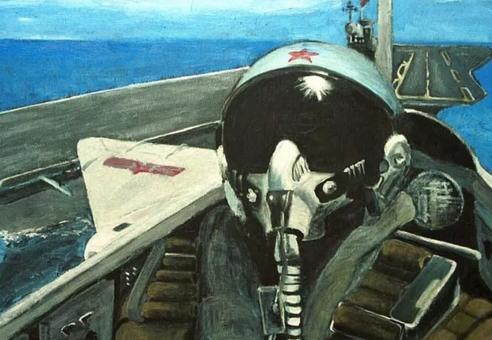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