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xieliaobaba.com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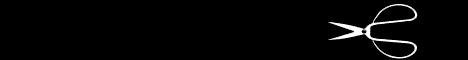 |
|
冷落誰都正常 文.焦國標 亨利.摩爾的雕塑品在北京遭遇寒流。寒流有多寒?11月9日那天我去中國美術館,上午10點半,中間那個大件展廳里算上我才有3個觀眾。于是媒體紛紛說:“中國人對亨利.摩爾的認識不夠”,“在北京幾所重點高校的調查顯示,90%的學生竟然對亨利.摩爾一無所知”,“錯過了這次機會,忽視冷落了亨利.摩爾,將是我們的遺憾”,諸如此類。喜歡與否,本無是非,媒體理應客觀報道,態度居間。如此異口同聲責備國人,我們不僅要問,這船到底歪在哪里? 藝術好惡這東西,從來就是有趕東集的,有趕西集的,有買蘿卜的,有買白菜的,火了誰預先難以逆料,實際上冷了誰都是正常。就說梵高的那頂向日葵,哪有什么準信兒,全是西方藝術品市場上波詭云譎所致。藝術品炒家的本事是找事然后造勢,藝術市場又有一種皇帝新裝效應,人人進來都是想投機爆發的,買方賣方誰也不把那邪乎的東西戳破,于是那陰差陽錯被選中的藝術品就跟鷂子翻身似的,誰也說不準天空里這個愣頭青究竟最終會翻多高,當然誰也估不透最后它會摔多死。 摩爾的雕塑品,有些大方之家說中國觀眾不懂抽象藝術,看著琢磨著它們像什么,真是“悲哀”。我倒是想反問一句:你們這些懂抽象的人士,看摩爾的作品難道就不聯想它像什么嗎?你說那是抽象藝術,那么它究竟抽誰的象呀?你就不琢磨這個問題嗎?一件雕塑品當前,什么都不聯想的,就只傻看,一準是白板。人的思維路徑就是碰見感不清的想把它感清,碰見說不清的想把它說清,我想任何行家看抽象藝術也逃不掉把它還原為具象。藝術品是有抽象具象寫實寫意之分的,可誰也不比誰更高(中國畫的工筆人物花鳥,陳逸飛油畫的吹蕭女,哪一點比抽象作品差呀),藝術評論家大可不必弄得好像誰將抽象藝術往具象上猜誰就“悲哀”,誰就是“沒有一個正確的審美角度”。搞藝術批評的比抓意識形態的還一貫正確,別的都是異端,是缺乏基本的現代學養之表現,比看見摩爾的作品就猜是熊還是是豬的普通看客更等而下之。 前一陣子達利畫展,比摩爾雕塑展紅火得多。達利畫本身只是海德格爾“一瞬間”理論的繪畫表達而已,其哲學意味實在寡淡得可以。可惜畫壇與哲學太隔行,就傳達這點兒哲學常識,一個世界級的畫壇大師竟出爐了。摩爾的東西也被貼上哲學突破的金紙,說上帝造人是完整一體的,摩爾的人像作品上竟然有空洞,這是“上帝死了”的美術表達。如此一來,摩爾不用說是畫界的達爾文和尼采。其實,這些說白了不過是圖解新潮哲學罷了,比圖解政治略好一點而已,沒必要上那么高的綱。美術與哲學是兩個王國,畫家就是畫家,畫作之美不容易說清,一定用哲學來哄抬物價,說穿了是把美術之王摁到哲學家門下當小學生。 有些觀眾明確說,不是藝術不好,是厭倦了操辦者、專家和媒體的共謀。操辦者是藝術掮客,說起來是藝術的信徒,卻隱隱約約一副賭徒的嘴臉,瞅空子發財,恨不得鼓搗一次活動就賺得錢袋子炸線。專家和媒體為討賞錢,甘心做提線木偶,口吻、嘴臉和程序全由藝術掮客輸入。《學習的革命》風波不遠,國人記憶猶新,到如今早落滾兒了,哪個中國人的學習因此發生革命了?技術性很強的東西尚且如此,何況藝術作品,對一般觀眾(非專業者)來說,看看也就那么回事,心不多生一竅,臉不多長一塊。經營藝術展的套路該翻新了。 摘自《深圳周刊》2000.11.20
|
|
.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