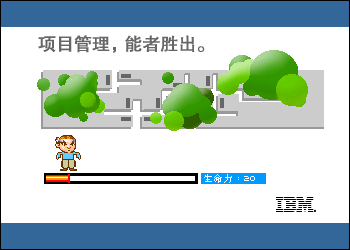李谷一的音樂是兩個音樂品種的結合體,一半是民歌,一半是通俗。
人如其歌,女兒肖一眼中的李谷一,一半是堅強,一半是脆弱。
當李谷一演唱《鄉戀》登上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的舞臺上時,她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藝的春天來了。從那時起,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余生的精力奉獻給中國的輕音樂事業。李谷一作為中國內地第一個流行歌手,這位中國通俗音樂從弱到強的見證人和親身參與者,成功地把西方的現代音樂理念與中國傳統的民歌結合改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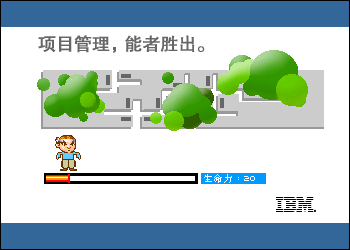
李谷一在觀眾面前表現的是自信和風光,她有《鄉戀》、《難忘今宵》、《妹妹找哥淚花流》等等風靡全國的經典歌曲。而她的另一面卻充滿坎坷。從她有膽量做中國通俗音樂的開拓者之時,就已經注定她的音樂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事實證明,命運就像老天早已設計好的一盤棋,她每走一步都有一招險情擋在面前。她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經歷:“1970年,因先前一出《補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視為修正主義黑苗子,抄了父母的家,我們被下放到偏窮的瑤寨,要靠著勞動‘工分’吃飯,一個年輕的生命懂得了生活的辛酸和磨難。1980年,在一曲《鄉戀》引發下,我成了中國樂壇上離經叛道的眾矢之的,招致了如同政治事件般的批評和批判,幾個月里眼中淌淚心靈淌血。1990年,后來被稱為‘中國民事第一訟’的官司,在河南南陽沸揚,那是國家制度與個人利益的沖突和對撞,卻把深同師生、親人間的情感撕裂給人看,事實澄清了,官司贏了,她的內心卻傷痕累累,痛楚至今。”而在2000年她又面臨“東方歌舞團事件”的風波,她在女兒眼中一直是刀槍不入的,卻被打擊得心灰意冷。
時光飛逝,轉眼20年,中國的通俗音樂已經從當年所謂的輕音樂變成R&B和HIP-POP的天下,還有人在意中國流行音樂的淵源嗎?在每個年輕人都能充分的享受流行音樂產業數量龐大的產品的今天,我們覺得有必要再來審視內地通俗音樂的起點——“中國第一個流行歌手”李谷一。
李谷一在事業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葉。就連給女兒起名字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在她和愛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肖一從幾歲就開始叫媽媽為“李老師”。因為“叫她‘李老師’她的反應特別快,而叫‘媽媽’往往要叫兩聲她才有反應。”
電話里,肖一的聲音聽起來很“爽”,嘹亮,很像她母親。不過母親甩不掉依稀湘韻,而成長在北京的女兒已經是一口“京片子”了。
我們倆再也沒有一同去過公共場所
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有些模糊,她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個月不在家,自幼母親對我的忽略讓我成了吃“百家飯”長大的孩子。1980年左右,媽媽在中央樂團做獨唱演員。而我還不到三歲,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單位的一個老師家。那個爺爺家住在一層,有個窗戶正對著媽媽單位的大門,每到下班時間,我就趴在窗戶前望著大門,一看見媽媽走出大門往這邊的宿舍樓跑來,我就高興得滿屋子地喊“媽媽!媽媽!”
四歲的時候,她干脆把我送出了北京,我在許昌的一個親戚家生活不到一年。我年紀太小,并沒覺得自己特別慘,但是多半年之后出現在父母面前的我成了個又黑又瘦的小孩,他們也覺得這樣不是事,無奈把我接回來生活。
我最需要母親照顧的年歲,也是媽媽的事業最繁忙的日子。我上幼兒園的時候,有一次淘氣爬鐵柵欄摔斷了胳膊,恰恰此時媽媽不在身邊。奶奶和爸爸帶我去醫院接骨,醫生把骨頭接錯位都不知道,打上石膏之后才發現問題,只能敲開石膏重新接一次。等我的傷已經反復去醫院看過三四次后,媽媽才騰出時間第一次看看我摔斷的胳膊。
從我很小,媽媽就不能帶我去公共場所,不逛公園,不去商場,因為帶我出門被人認出來會非常麻煩。有一次她帶我去湖南一家很大的百貨商場,結果母親被商場的售貨員認出來,激動得大聲喊:“她是李谷一!”其他的售貨員和商場的顧客也聚過來和她握手,說話,要簽名。三四十個人圍了好幾圈,結果把我擠出去了。我傻愣愣地站在一邊看著這場面,沒哭,只是覺得特別沒意思。母親只能從人縫里看見我站在遠處,直到滿足所有人的要求,才走過來帶我走。從那次起,我和媽媽彼此心照不宣,我再沒提出過要她帶我出門的要求,而她也不會提這樣的建議。
1985年左右,母親沉浸在中國輕音樂團繁忙的工作中,臺前的演員、樂隊以及所有幕后工作人員都由她一個人管理。可以說,媽媽99.9%的精力都投入在團里,她對演員和學生比待我更好,她沒給我開過一次家長會,我學習上的事情也無暇來管。所以小時候我老覺得自己不是我父母親生的。那時我們家就像個考場,只要媽媽在家,每天就跟走馬燈似的沒完沒了的來人。全國各地各式各樣的年輕演員找我媽媽,一進我們家門,說不了兩句話就對著我媽唱歌,希望能投在她的門下,進她的樂團。
“李老師”認為我沒什么培養價值
母親對女兒的忽視雖說不是件好事,但是成就了我獨立的性格,上高中的時候我就離開父母搬出來單住。因為我住的那套房子和他們離得挺近,每天見他們的機會只有吃晚飯的時候,吃完飯我就回去寫作業睡覺。而母親往往有很多開會、采訪、出差的“外事”活動,跟她見面的機會就更加少。
我的家庭教育很嚴。我父親成長在軍隊家庭,很怕我養成嬌氣不講理的小姐脾氣。小時候家里做飯從來不會考慮我的口味,即使做的是我不愛吃的菜,他們也不會遷就我或者給我開小灶。治我挑食的辦法也很絕:不愛吃餓著別吃。他們吃完飯會把剩下的飯菜都用碗扣起來保溫,等我餓了自己就知道找飯吃,所以我現在一點兒也不挑食。
母親最初打算把我送到沈陽的一所藝術學校,當時那所學校在中國的藝術學校里算得上一流。但是我父親不同意,母親想想我一個小孩在外地也覺著心疼。不過更關鍵的原因是“李老師”在綜合考量我的實力之后,認為我根本不是搞這行的材料。缺乏表現欲,膽子小,當眾表演愛怯場,沒什么培養價值,這就是“李老師”對自己女兒的評價。而我本身對媽媽整天癡迷的東西好像有種天生的抵觸,沒意思,沒新鮮感。
有朋友勸我說,你也唱歌多好啊,有你媽什么事都好辦。我一想也是,就跟我媽說:“我把你那些有名的歌都改成rock&roll出張專輯,怎么樣?”結果是我爸第一個不答應:“你要造反呢?!”
都說婆媳難處,但媽媽對奶奶格外親近。我奶奶晚年得上老年癡呆,病到晚期精神恍惚,言語失常,可是直到最后她還總是喊我媽媽的名字,喊“谷一吃飯!谷一吃飯!”惦記著讓我媽吃飯。
“長相占先”之說是一場誤會
心直口快的性格給媽媽帶來了不少麻煩。那一年,她在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上,因為“長得漂亮一些的演員更占便宜”這一句話引起軒然大波。事后,不少朋友追問她是不是說了這句話,一些網站上的網友們有的疑惑,有的質問,有的觀眾寫信打電話到東方歌舞團里找她問清楚,“李谷一是文藝界前輩,為什么會在這么多渴望踏上藝術之路的年輕人面前說出這樣不公平的話?”
那天的現場直播我和父親都在電視機前,也許現在的生活節奏太快,只有她身邊的人能夠會意她要表達的意思,而大家都只抓住了她那一句話。和我媽媽一輩的歌唱演員,哪個不是憑一把好嗓子實實在在的唱出來的?我媽媽最受不了“包裝”這兩個字,看不慣沒真本事光憑長相的年輕人。她本意是想說,藝術是全方位水平的綜合產物,注重形象是作為一個演員的基本素質,長得漂亮些的演員觀眾更喜歡,更容易受歡迎。媽媽每每在公眾場合露面肯定要經過精心裝扮,她的原則就是尊重觀眾。多年的職業要求很自然的形成她穿衣打扮的品位,即使是在生活中隨意的穿著,她比我會搭配,而且同樣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比我更“有味兒”。我想對這個觀點任誰也不會說出什么不是,只不過當時媽媽只把她主要的意思說出來,沒容她解釋清楚便鬧出誤會,說她“看人有色”。之后我和父親也小小的聲討她一番,“李老師”還是虛心接受的。
多災多難的媽媽
媽媽的性格很復雜,是個矛盾的集合體,說也說不清。有人說她是事業上的女強人,可是她最容易動情,愛掉眼淚;然而每當她流過眼淚之后,并沒有在眼淚中消沉下去,再次出現在大家面前的李谷一更加堅強。
她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80年,只有三歲的我對那次災難還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陪同在媽媽身邊的父親與她共同經歷著那次沉重的打擊。面對來自全國的批判,整整15天媽媽處于嚴重的失眠和精神衰弱中。她弄不明白,《鄉戀》只是一首小小的歌曲,為什么會遭到如此嚴重的譴責?在1983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由于全國觀眾要求強烈,媽媽終于演唱了這首被批為“廁所歌曲”的《鄉戀》,媽媽感到她實現音樂理想有希望了!
而后她在多番或大或小的挫折中經受著痛苦,但是從未一蹶不振,反而越挫越勇,不論多難她都能自己挺過去。但是最近一次“東方團事件”的打擊讓我明白,其實她并沒有看起來那么堅強,我第一次知道她也有這么脆弱的時候。2000年,我父親在云南報病危,母親前往照顧他,父親尚未痊愈,因為“三講”開始,母親被緊急召回北京,焦急中也病倒在醫院。母親因為她直爽的性格捅了馬蜂窩,在“三講”期間遭受到不公待遇,我第一次見她這樣的焦慮和沉悶,頭上有兩塊地方頭發掉得一根不剩,一夜之間,原本朝氣蓬勃的母親一下老了很多。
李谷一反訴:我不是強者
我一向對女兒要求很嚴,但有時他們不理解,畢竟年輕人和我們的想法不一樣。我對自己子女的要求是只要自食其力,靠智慧、勞動成家立業就行了,沒必要期望太高。
肖一一聲“李老師”叫了我二十多年,大家在一起的時候她不想顯得特別,就也隨著我的同事和學生們叫我老師。肖一不是打著父母的名字出去招搖的孩子,她曾經在中央電視臺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因為工作關系一直和央視有比較頻繁的接觸,也有不少熟人,但是直到她離開央視,除了那幾個和我熟悉的老導演和演員,肖一小的時候跟他們見過面所以認識她,其他身邊的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這回事。
說到家庭,我這些年來有“三個愧對”。一愧對父母,我父母都已經是九十多歲的老人,我母親現在病在醫院,我不能盡孝;二愧對丈夫,對丈夫我沒有盡到妻子的責任,這么多年來我們兩個人比著忙,我演出繁忙,而他因工作經常不在家,聚少離多;三愧對女兒,在她最需要母親關懷的時候,我卻沒能給她什么直接的教育。事業上的堅定使我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比常人更加脆弱。
我小時候過得很苦,十幾歲離開家,不像現在的孩子在父母身旁享福,一切都要靠自己奮斗,可能正是因為經歷得多了,所以體會很深,歌里唱出了感情,就很容易掉眼淚。回頭想想這幾十年,經過一波接一波的打擊之后,我有時懷疑自己一直堅持的想法是不是錯的?不應該那么認死理。我是從過去走過來的人,一直堅持著傳統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快人快語確實造成過一些誤會,但是面對大是大非,見著現在社會上的不公和那些扭曲的人際關系,我很難想象,也不能接受。
我愛人說,他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掙多少錢,而是看到我的歌迷除了那些從當年伴隨我至今的老歌迷外,還不斷有年輕的朋友甚至初中生成為我們知音。被吸引進來,才是他最大的欣慰。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