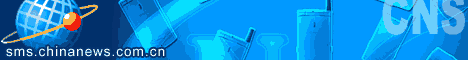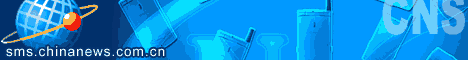(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民意”開始在網絡上現身,不是噓的一聲,而是轟的一聲,不是意見領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結隊。在缺乏程序正義的時代,“網絡民意”并不是程序正義的對立面,而是微不足道的替代品。
警惕“民意”是警惕一種會在民意前失控的制度,而不是警惕站在制度門外的“民眾”,更不意味著知識精英對于一般民眾的藐視。
從劉涌案到蘇秀文“寶馬”案,源自網絡的民意似乎開始撬起一個又一個案件。我們不難在網上看到鋪天蓋地的喊殺之聲,這也許將誘發2004年中國社會法治進程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網絡就是一個虛擬的廣場。多年以來,你在現實的廣場上看不到熱氣騰騰的民意,你在平面媒體上也只能讀到少數精英的理性評點和被他們“代表”了的間接民意。所以在未有網絡之前,“民意”是一個隱身人。直到去年孫志剛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民意”開始在網絡上現身,不是噓的一聲,而是轟的一聲。不是意見領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結隊。
但學者們對民意登場的評價也出現了分歧,以往常說“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民憤在哪里呢?在一個無法為民意表達提供足夠制度平臺的稀薄的公共領域,所謂民憤就像游擊隊,埋伏在來自街道角落的臟話和家家戶戶的廚房里。現在,借問民憤何處有?牧童遙指互聯網。民憤就是成千上萬的帖子,就是變成了印刷體的浩蕩唾沫。于是一些學者開始擔憂,在劉涌案和蘇秀文案中,民意已經干預甚至脅迫了司法,那些表達了民眾樸素正義觀的喊殺之聲,是否傷害了一個法治社會引為驕傲的“程序正義”?難道傳說中的“多數人暴政”,來得如此之快,如此不講道理?
應該說對民意的警惕和預防,的確是憲政民主的一個基本理念。憲政的意思不僅是限制政府權力,也要限制“人民”的權力。因為憲政的實質就是限制主權者,“主權在君”就虛君,“主權在民”就虛民,主權在老婆就要“虛妻”。“虛民”有兩個最重要的手段,一是代議制度,二就是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
一種溫和的看法是,建議通過陪審團制度來吸納民意,一般認為陪審團是無法被收買的,陪審團也因為利益立場中立而能最大化地實現程序正義。不過我們看在擁有古老法治傳統的英國,歷史上一些著名冤案卻也幾乎都是陪審團在激情之下做出的。如1953年一個有智障的青年人戴瑞克,因他的同伴殺死了一名警官潛逃,而被陪審團當作替罪羊裁定有罪。對這一案件的反思和抗議直接促使了英國死刑制度的廢除。
民意或民憤的非理性,可能出自一種移情作用。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人們很容易把長期以來或在特定事件中激發的憤怒,遷怒于一個具體的被告,這時對他的審判就成了一種政治儀式,對他的懲罰也成了一種公開的獻祭。如在英國的上述冤案中,這樣的“民意”滲透進陪審團,擁有生殺大權,就十分危險。
民意可能是非理性的,還因某些時候多數人的意志和欲望完全可能受制于主流的意見 某些場合下越是非理性和情緒化的意見就越是容易成為主流。
但在劉涌和“寶馬”案中,網絡民意的沸騰并不是負面的。批評民意的人沒有注意到“網絡民意”只是一種制度外的輿論。它并沒有進入和干擾訴訟程序。一些學者對案件中沸騰民意的某種敵視顯然是戲劇化了。輿論只在制度和程序之外鬧騰 而一種良好的司法和政治制度就是要經得起人們站在制度外鬧騰。在法庭外、議會外和政府大樓外鬧得再兇,一種法治秩序也應該具有做出吸納或拒絕的理性能力,并因為司法制度的運作具有程序正義,無論這次吸納或下次拒絕都不會危及政治秩序的說服力。
當然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制度環境,但你只能去要求一個在民意面前表現得更好、更得體的制度,而不能要求民眾在受到傷害后,永遠像紳士一樣保持理性和矜持。
民意自古以來就是非理性的,否則還要憲政制度做什么呢?警惕“民意”是警惕一種會在民意前失控的制度,而不是警惕站在制度門外的“民眾”,更不意味著知識精英對于一般民眾的藐視。
“正當”不是一個理念,而是一種稀缺資源,是一個經驗上的判斷和積累過程。只有在一個罪人因為尊重程序規則而被漏網之前,先有十個、一百個無辜者因為尊重程序規則而受到保護,這樣的程序才可能“正義”,這樣的代價才是一個轉型社會可欲的。這樣的“程序正義”才和中國當代社會有血肉關系,才能贏得老百姓對法治最起碼的信心。否則“程序正義”就是一個虛假的和中國的民眾無關的理論假設。
司法獨立是最基本的程序正義。在缺乏程序正義的時代,“網絡民意”并不是程序正義的對立面,而是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如果司法在這樣的民意面前頻頻失態,那么民意就可能成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