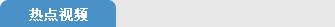- 中國極地中心主任:應制定更有雄心的南極科學計劃
25年前的11月20日,中國首次南極考察隊踏上了遙遠的征程。然而,在那支591人的科考隊伍中,為什么只有五六名科研人員?
“先站住腳跟。”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漢解釋。近10年來,今非昔比。考察隊中科研人員比例已經達到60%。
“南極研究是個國際大舞臺,必須拿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與國際同行競爭。”我國最早踏上南極洲的科學家董兆乾一語中的,“現在更強調,要在硬件條件提高的基礎上,做出高質量科研成果。”
在南極放大中國的聲音
我國南極科考起步較晚,在開始的那段日子里,國際舞臺上很難聽到來自中國的有分量的聲音。
“以前參加國際會議,發言無非就是介紹在長城站、中山站做了什么,提出的目標都是泛泛的宏偉規劃。”劉小漢說,由于拿得出手的成果非常有限,每次發言順序也比較靠后。
現在有了改觀。“我們不光說做了什么,還提出新發現、新觀點,提計劃時也會非常具體。會后總有人遞來橄欖枝,‘咱們能不能合作?’”劉小漢說,這是自己25年感到的最大變化。
董兆乾也有同感。1980年,他隨澳大利亞隊赴南極考察,盡管樣品采集、文章撰寫工作都是他完成的,但署名時他也只能排在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澳方科學家,因為項目是人家的。
據介紹,25年來,我國已經組織了26次南極科考,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今年6月4日出版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極地海洋學研究室主任孫波的論文,證實冰穹A是南極冰蓋的起源地。這篇由中、英、日三國的9位科學家合作完成的論文引起了很大轟動,孫波是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
美國WoS數據庫收集了我國自1982年以來,在世界核心期刊上所發表的有關南北極的研究文章,數據顯示,我國科學家每年在國際頂尖雜志上發的論文增長迅速,1982年到1985年只有9篇論文,2006—2008年三年就發表497篇。
我國應制定更有雄心的南極科學計劃
“一船三站”、建造新的極地考察破冰船,爭取盡快添置固定翼飛機……短短25年,從極地考察規模和能力上看,我國可與美國、俄羅斯、英國和德國等極地強國比肩。
“問題是,在擁有了良好的硬件支撐平臺后,我國極地事業迫切需要雄心勃勃的科學計劃來引領。”中國極地中心主任楊惠根所言的“雄心勃勃的科學計劃”,意指圍繞當前科學前沿上的大科學目標。他希望借助大科學目標的持續推動,穩定并擴大科研隊伍,推動我國極地事業躍上新的臺階。遺憾的是,現在的硬件平臺本可以做更大的科學研究和探索,但相應的科學計劃卻顯得有點滯后。
據介紹,冰川深冰芯科學鉆探計劃被認為是未來3—5年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研究,但由于缺乏體制保障,加上研究隊伍本身原因,目前獲得的支持并不多。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我國具有領先優勢的地質理論、地球化學、天文學研究等領域。
從數字看,我國極地科考經費增長迅速。但每年國家財政撥款里,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四分之三甚至更多的經費都投在硬件條件改善上,真正能用于科研的經費不多。
董兆乾試圖通過申報支持力度更大的國家課題以推進研究。他剛參加了一個項目的答辯,沒有通過,“你根本沒法和人競爭。”
申報原則的其中一條就讓他不戰而敗。按照要求,項目需圍繞我國社會、經濟和科技自身發展的重大需求,解決國家中長期發展中重大關鍵問題。“但對從事兩極基礎研究來說,成果離應用還有很長一段路,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昆侖站要變成有人值守的越冬站,需要等待科學需求的充分發育,與保障能力的快速發展匹配起來。”楊惠根告訴記者,在《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等綱領文件中,極地研究 “可以找到位置,但缺乏明確指向”。他希望能從政策和機制上鼓勵“中國雄心勃勃的南極科學計劃的誕生”,做強我國的極地事業。(陳瑜)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