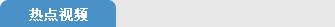- 社會組織發展引資源爭奪戰 欺詐挪用善款亂象凸顯

繁華下暗藏隱憂 社會組織管理尋求突圍路
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依法登記的數量已超出40萬個,服務范圍滲透到科教文衛體、勞動、民政、環境保護、社會中介服務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踐表明,社會組織是溝通政府和群眾的一座重要橋梁,有助于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良性互動。但不能否認的是,社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亂象,如用欺詐性手段爭奪社會資源、內部交易等等。而這些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原有社會管理方式和手段的滯后。對于這一不盡如人意的現狀,各地各部門紛紛走上了對社會組織管理進行變革的探索之路。
在北京市朝陽區國貿繁華地段的一間略顯擁擠的咖啡屋里,記者見到了一家民間艾滋病防護組織的創立人王為(化名)。
正是秋意漸濃的時節,窗外射進的陽光讓人感覺似有若無,柔和地披灑在享受咖啡醇香的人們的身上。
王為語氣平和地向記者介紹著艾滋病防治組織的現狀,聲音并不算大,但屢屢提及的“艾滋病”、“同性戀”等字眼,卻讓周圍的人不時投來異樣的眼光。
在王為娓娓道來的講述中,記者卻解讀出了另一層意思———盡管艾滋病防治組織的產生與發展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卻和其他正在繁榮發展的社會組織一樣存在著共同的問題。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服務社會群體的意識欠缺,爭奪社會資源的意圖強烈”。
溯根尋源,“社會管理手段的滯后”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記者了解,對于社會組織的管理長期以來都不盡如人意。正由于此,各地各部門一直都在諸多方面積極尋求管理手段的突破。
隨著更多資源的注入,各同性戀防治組織之間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爭奪相關資源的斗爭中;而這正是諸多社會組織的“通病”———為了獲取資源,可以相互指責、報復乃至造假,卻在不知不覺中丟失了“服務社會群體”的意識
王為的講述把話題拉回到17年前。那是1992年,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悄然出現。隨后,中國同性戀志愿者網絡開始形成。而這也是艾滋病防治社會組織出現的前奏。
王為說,在同性戀社群組織發展史上,有兩件事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艾滋病和互聯網。最終形成的結果是,很多同性戀社群組織都以艾滋病防治的名義做事。
據王為介紹,由于男同性戀一直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有關部門為了詳細掌控這一人群的動向,更好地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始主動與同性戀社群組織聯絡并參與建設。
然而,隨著更多資源的注入和社會組織的興起,各同性戀防治組織之間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爭奪相關資源的斗爭中。
此時,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是———2001年,同性戀脫離了“性變態”的語境;另一方面,各種用于艾滋病干預項目的基金紛紛出現,使得許多同性戀社群組織都匯聚在防控艾滋病這桿大旗之下。
王為告訴記者,艾滋病防治基金都是通過政府部門,比如各地疾控中心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分配到各個社群組織。“在分配資金時,往往根據各個組織之間抽血檢驗的人數來進行。因此,許多和艾滋病防治有關的社會組織都熱衷于拉人抽血。”
此外,王為還告訴記者,在許多和艾滋病有關的社會組織之間,為了爭奪資源,會出現諸如摩擦、指責、報復甚至采取極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傾軋的現象。
據記者了解,上述問題不僅存在于與艾滋病有關的社會組織中,很多領域的社會組織都存在利用欺詐性手段爭奪社會資源的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家民間教育組織出爐了一份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犯罪現象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稱,數據主要源自某地看守所及北京地區的流動人口聚集地。此份報告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但記者和北京一家報道過這份調查報告的媒體的記者核實時得知,這位記者在隨后的調查中發現,報告的數據有很多是虛構的。這家民間教育組織的負責人后來也承認了這一點。
對此,北京一家公益組織的創立者田坤向記者談了他的個人看法。他說,他不能隨意揣測這家民間教育組織造假的真正動機是什么,但多年的經驗也讓他對業內的“潛規則”有所了解:一些社會組織造假是為了獲得相關的資源。說得更通俗些,就是制造社會影響從而方便找人要錢;還有一些社會組織是在拿了人家的錢之后,為了好交差而炮制出一份調查報告。
田坤說,目前社會組織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服務社會群體的意識欠缺,爭奪社會資源的意圖強烈”。此外,還應加上兩點,“財務狀況較亂,從業人員不規范”。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